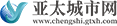(二)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“鬼者,涿野之夷也。首生枝角,体披斑纹。性凶好斗,不修礼政;筋强骨壮,无识乐雅。好涉徙丛泽之间,攀引重之中,行迹无常。不通经义,难于德教,唯善力役也。”
——《琼东方物志》
漆黑。
漆黑之外,唯余漆黑。好像悬浮在水中,四肢被托举着,可又一点光也没有,似乎是在一片深海。渊下的水流很不宁静,有声音传过耳边。极力地看去,在极深极深处蜿蜒着那样长的庞然大物,像盘山的车路一样环绕着上浮。这一下时,觉得身上一阵恶寒,手向上伸去,划动,本能驱动着身体远离。
然而无用。
那巨怪已扭动着围住了自己。倒三角状的头颅经过自己时,能看见他的眼睛,如血般炽热通红。它的身体长度已经不重要了,毕竟现在自己毫无挣脱的可能。巨怪覆鳞的身体围成一堵墙,向处在中心的自己收缩,就在自己几乎不能伸直手臂的时候,那些鳞片开始崩落,裸露的脆弱的肉上渗出紫红色的血。“围墙”垮塌了,只有白骨在缓缓下沉。那颗头颅也沉了下来,慢慢在水里打着旋,带出一条紫红的血雾。
最终,巨怪的头颅不再下沉,停留在与自己同一高度上。它血红的眼睛盯着这边,眼瞳是一条竖线,同人们所熟知的冷血动物一样。
这时候,先前所听见的声音越发明晰了,杂乱的音节以极为奇怪的方式组合了起来,却诡异地使人听懂了:
“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。
那颗头颅上剩余的鳞片也开始剥落,每一片都渐渐发白,在这暗渊中扭曲成髑髅。在它们的前额上一概长着一支或二支角,犬齿略长,显然是“涿野鬼族”的特征。
因此惊诧,讶异,不知所措,被那一切白森森的东西沉入渊中。
直到晚风吹得袁谷打了个喷嚏,他的意识才真正从梦中抽离,回想起现实。他,皇帝亲授的“抚海将军”,正完完整整地活在康和二十三年,非常安全地处在羽户省下川府, 名正言顺地住在抚海将军府中,问心无愧地享用十年戎戍换来的封赏。他重新躺下,深呼吸平复内心的波动。他反复告诉自己,是的,安全且正当,没什么可多虑的,当下的一切都很好,并且会越来越好。这个噩梦不过是因为自己还没习惯睡软床而已,加上入秋以来天气渐冷,有些不适很正常。他翻了个身,将手伸出床沿,拿起床头柜上的一个罐子,抖出一颗定心丸,嚼烂后咽下。
抚海将军府内一片寂静。院子里,先前那些叱咤了一个盛夏的蝉与蟋蟀如今死在寂静里,它们的尸首被蚁群肢解,拖运回蚁穴当中,充当它们的的养料。
夜晚沉默地走过,朝霞昭示白昼。
城郊的山林里,刀匠屋顶的烟气从未断过,每块要被铸成宝刀的好钢都要经历这样的烧锻。木门被叩响,守着炉火的学徒忙去开门。
“啊!将军大人!失礼失礼,请进!”
“多谢了,阿平。渊上师傅呢?”
“师傅正在休息。师傅最近身体很不好,将军要见一见他么?”
“嗯,让我看看渊上师傅的情况吧,也许我能帮上一些忙。”
走进渊上康成的房间,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躺在打了好些补丁的垫子上,身上的被单也没完整到哪里去。
“阿平,出什么事啦?——啊,是袁将军啊。”
袁谷在渊上旁边的坐垫上跪坐下来,行了一个礼。渊上试着起身,但被袁谷和阿平制止了,便就这么躺着。
“袁将军送来的刀,真是给老身开了眼啊。”
“多谢渊上师傅夸奖。嗯,那刀在六年前被一只大祟折断了。在下找过许多刀师,六年来没有一个刀师愿意接受委托,他们都叫我另请高明。也是幸运,遇到了渊上师傅。”
“哈哈哈,将军您抬举老身了。老身锻刀几十年,是个爱刀之人,恰好袁将军的那把刀有着非凡的气质,无论是刀镡的制式还是刀刃的用料都很不一般呐。老身也是斗胆尝试,毕竟这样的好刀,哪怕只是去修复它,也是很值得铭记的事啊。”
“渊上师傅说得在理。那把刀叫‘御霆斫光’,是我袁氏家传的宝刀。早在太祖还没有赐我氏以‘袁’姓时,我伊歧氏就已经锻铸了御霆斫光。到我这儿时,已经不知斩杀多少邪祟了。”
“好,好,是把好刀。”渊上停了一会儿,接着说:“袁将军,您从军多久了?”
“康和十三年,到现在已经十年了。
“这样啊……嗯……我们涿野鬼族已经很久没有像袁将军这样的人物了。袁将军,实在是我族的骄傲啊。”渊上仰面看着天花板,那些木板上长着霉斑。袁谷在一旁沉默着。渊上的角早已褪了颜色,只在双角尖端处有些许黑色。
“时间到了。”良久的沉默后,渊上开口。
“什么?”
“御霆斫光的时间到了,袁将军。”
阿平从火炉中夹出坩埚,其中翻滚着铁水。御霆斫光摆在一块模具上,沿着断面紧紧贴合在一起。
“老身试过许多寻常方法,袁将军。”渊上说着,此时他的脸映着炉火,比先前在卧室中精神不少。
“但一概不奏效。这把刀极耐高温,没法重熔再铸,上面还附着法术——许是附雷后的残留——修复药剂和法术完全没用。”
阿平将滚烫的铁水倒入模具,那铁水也只是在御霆斫光的边缘处“滋滋”冒泡。“所以老身决定用鬼族先祖们流传下来的方法——老身当然知道外界都说这法子只是个传说。但是,袁将军,老身在少年时候确实见过血铸之法,而那些行使此法所锻造的刀,也的确有传说般的品质。”渊上用双手奉上一把精致的匕首,柄上包着鲨鱼皮。
袁谷看着他,没有说话,他的脸背着炉火,看不甚清楚。
“血铸之刃,唯奉一人,忠烈至诚,犹同一身。”
于是袁谷接过了七首。
“不必再说了,渊上师傅。我知道该怎么做——”
他割开手掌,向下对准御霆斫光的断面。
“我也……听闻过这个法子。”
当渊上念起那些古老失传的文字时,袁谷手掌上流出的血汇聚成一条线,扭动着伸向御霆斫光,像一条赤练蛇。那些凭着发音口耳相传而内容已无人知晓的篇章,伴着琼东一带特有韵律环绕在房间内,使袁谷想起康和十三年的饥荒还未到来之前,母亲最爱给弟弟妹妹以及曾经年幼的他歌唱的摇篮曲。
伤口已经不再渗血,古曲已然停歇,阿平又拿起钳子,夹住那把刀,插入水中淬火。那“吡喇——”的响声,让袁谷联想到十年来听到过无数次,却没在“柳王爷”那儿听到的:
——那最后一声哀嚎。